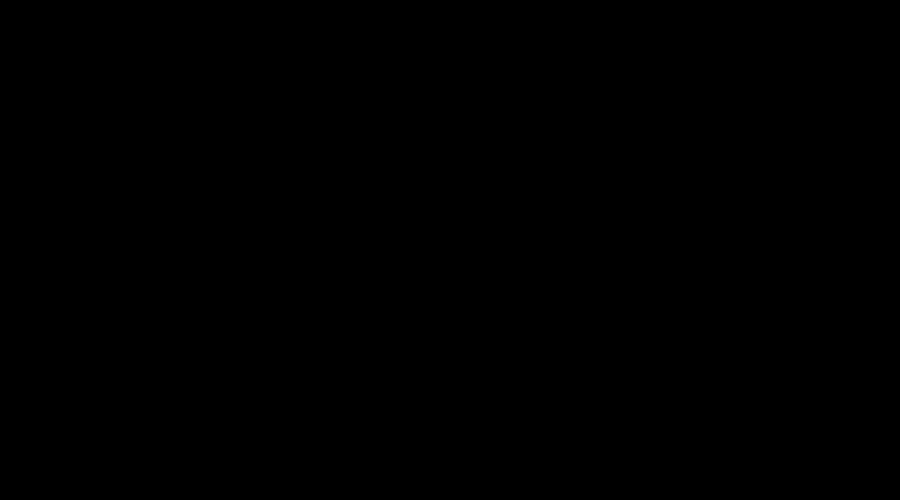再次拿起铅笔,生疏地将笔身夹在大拇指和食指中间,望着眼前的画板,你的脑海里仅仅只有一双手。
颤抖的手。
你还记得,上小学那会,铁北大片的平房还没拆迁。七拐八拐胡同与横穿东西的马路连接在一起。铁北人如果问起路来,得到的答案肯定不是左转右转,而是一个方向和一句话:穿胡同走。
于是,每当放学,一次次穿越陌生的小巷胡同,都像是一趟探险。你见过杂草荒芜,颓垣断壁的荒宅;见过大院深宅,热闹非凡的庭院;见过熙熙攘攘,香气贯巷的磨坊;见过争吵不休,哭声幽咽的人家。可唯独那个下着雪的黄昏,你在一扇锈红的铁门前驻足,只因门上用粉笔写着几个隽秀的字。
“郑燮画室”
郑和画中间的字你记不清了,或许是因为那字太过复杂,对于那时的你着实难记;或许是因为那粉笔字日晒风吹侵蚀了样貌。总而言之,那段时间你刚学了郑板桥的《竹石》,稀里糊涂地就记作了郑燮。
你不会想到,多年以后,当你手握铅笔,面对画板,脑海里除了那双颤抖的手之外,记不起任何关于那个画室的细节,就连画室里的那个八十多岁的“郑燮”,你也完全忘记了容貌,你的记忆里只剩一双颤抖的手。
家里人受不了你的软磨硬泡,尽管他们并不理解外面好好的绘画班不去,偏偏要去这样一个巷子深处的平凡宅邸。总之,在那之后。你如愿成为了郑先生的学生。
锈红的铁门后,先是一小段不过几平的廊形庭院,一侧是路,一侧是种的白菜和大葱。后院的房子也不大,顶多七十平左右。土炕和客厅相连或是说那房子压根就没有客厅,靠窗的那一小片阳光直射的地方,整齐地放着三个画架。
你只觉得这是美,庭院,阳光,居舍的美,你说不出,但你惊艳于这的朴素。
那年郑先生刚好八十,苍颜白发,声音却温润凝实。身着暗红色衬衫,还有一条不知道多少个年头的蓝色长裤。他笑眯眯的看着你,问你的名字。
郑先生的家里一般是三个人,他、老伴、孙子。郑先生的老伴你是一点印象都没有了,但当你将思绪凝落在这几个字的时候,却能感受到某种舒适。是的,你对于郑先生的老伴的记忆,只剩下一缕细碎的感觉。
至于郑先生的孙子,你一定记得。孙子的大脑发育不正常,亦或者是幼时生了什么脑疾。总而言之,郑先生的孙子,智力不大健康。不过,若是送到特殊儿童学校进行教育倒也还好,问题是郑先生一家都是朝鲜族,特殊儿童学校的老师无法和这孩子沟通,而铁南的朝鲜族学校不愿意收这么个学生,于是,这八岁的小孩子只能留在家里,在画板前勾勒奇怪的纹路。
那时候你也不过十岁,幼时单纯的机心让你并不是很喜欢这个孩子。不单单是因为他的胡乱涂鸦让那时的你十分看不上,还因为他偶尔会在你画画的时候在一旁吵闹。
就这么在这朴素的画室学了几周,或许是因为你的天赋,又或许是因为郑先生的教学,你的水平突飞猛进,才一个月,就画出来了一副素描。素描的内容是一个杯子。装着半杯水,被顶光打亮的杯子。
那是一幅如同预言般的画作,在你往后的十几年人生里,你永远可以看到这杯子的影子。半杯水,不空不满,无色无味。你想起某个冬日的夜晚,你因为一次次的挫折垂头丧气的走在路上。手里拿着酒瓶,最后瘫软在一根路灯下。在你双眼将要进行最后一次抗争着酒精的开合时。你看见路灯那暗黄的灯光穿过绿色的啤酒瓶口绽放出神秘的绿光,你看见啤酒沫在酒瓶的中间无奈着兀自摇晃,你看见沉默的气泡在某处生出又毅然决然地扶摇而上。你看见内心深处猩红的念想却在不经意间野蛮生长。
你于是闭上了双眼,看见了半杯水。
后来的你对这段记忆有着莫大的执念,你很多次想讲给别人听,却又觉得这应该是只有自己能明白的事情。但无论如何,故事的源起,应是那个苍颜白发,面带笑容,朴素温润的如同一杯水的老人。你本以为自己永远可以记住他。
沉寂的记忆业已模糊,你开始意识到所谓的过往早已成为了一场消逝的幻梦,你于是下定决心要把这份折戟沉沙未销的残铁打磨出往日的光亮,你顺着记忆继续思索下去。
郑先生的一节课只要十块钱,就算是在那个时候,这学费也是十足的便宜了。你还记得他曾在你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拿出一本《中国画家大辞典》,翻到他的名字,用颤巍巍的手指给你看。
“这是我的名字。
能被这本辞典收录的人,一节课却只收十块钱,想到这,你心中涌起莫名的羞愧。那时的你很好奇,抖动的如此厉害的手,如何可以坐在画板前面下笔。郑先生平日从不作画,就连给你上课也只是在一旁指导,不会亲自动手。直到你开始画第二幅画。郑先生要你以他的一幅画为模板,做出一个一样的人像,一位少女。穿着翻领大衣和过膝百褶裙,头发微卷,蔓延到少女的腰间,氤氳的像一团带着纹理的霞雾。少女的眼睛干净纯粹,但这也正是问题所在。当你花了三周的时间画完肢体,衣物,头发,手指,你陷入了停滞,你理解不了那样的眸子。你于是向先生求助。
“所有艺术的复现,要基于对美的理解。”说到这,郑先生似乎想起了什么,兀自的愣了一下。“你不懂她的眼睛,并非不懂画法,而是你不懂她的心情。
“那她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呀?
郑先生又愣了一小会,“或许我也不能完全理解。”随后拿过你手里的画笔,对着画板上你那少女的眼睛的位置,戳了上去。
的确是戳,不讲握笔力度,姿势,角度,兀直地戳了上去。但令你一辈子都难忘的是,那颤抖的手在落笔的一瞬间变得平稳无比,每一条线条都完美的没有任何瑕疵,尽管在你身后一边给你讲解一边作画的郑先生甚至控制不住嘴角的口水(郑先生的嘴一直都合不上,或许是某种怪病),滴落在你的头发上你却浑然不知。
那一刻属于美,属于启蒙,属于那双世界上最纯粹的眸子,属于郑先生小心翼翼保存的往事。
你一直在想,那或许就是郑先生的女儿。
在画室的日子,从未见过郑先生的儿女,似乎永远都是和老伴孙子在一起。郑先生的儿女在哪里呢?若是郑先生八十岁,那也有可能是他的曾孙吧。那为什么,对于那样应该有三代或是四代的家庭,却只有三个人。
或许他的子女已经早逝,在死寂与粘重的黑色空气里,陪伴他的画作是他孤独的影子。
你忍不住继续思索下去。
或许郑先生并不像我眼里看的那样轻松,命运的丝绳正捆绑着他,在没有观众的舞台上,他一个人默默审视自己的影子。审视苦难,命运和呐喊。郑先生的儿子应该是某个政府部门的公车司机,你所生活的那个与朝鲜接壤的小城镇里,上过几年学的朝鲜族人都会选择这份工作(除去开车还算半个翻译)。或许某次开车的时候出了事故,或许是工作上的压力让他对生活产生了厌烦,又或许不过是某一个下雪的冬天脚滑摔倒在某块尖石上。总是,死亡不过是苍茫天地间荒诞的一束,却也是某个家庭脆弱的全部。
又或许郑先生还有一个女儿。那女儿幼时怕生,就连看向父亲的时候都怯生生的。她有一对漂亮的眸子,纯粹通透,像是夜里闪烁着的透亮的星星。女儿十几岁的时候开始叛逆,单纯的眸子开始闪烁着斗争的光。或许是因为耳钉耳洞,或许是因为早恋,又或许是因为那些属于那脆弱的家庭的数不清的矛盾。在某个夏天的夜里,女儿离家出走后再也没有回来。
晚年的郑先生开始审视自己的一生,审视自己在一次次荒诞的选择中踏上了苦难的道路。可这时的他才恍然发现自己的孤独,在一个个沉默着的夜里,他在床上无数次翻转自己的身体,直到房间另一侧的窗外传来清冷的晨光。但已有压力让他不得不购置几个并不需要的画架,收着十块钱一小时的学费,在如血的残阳下,显露出最后的,温暖的光芒。
可谁又能真正读懂他的孤苦。就好像你,当你意识到这破碎的记忆里有着一双颤抖的双手时,当你顺着自己的思索勾勒出郑先生苦涩的一生时。你也丝毫不能完全理解郑先生。
这世界上的苦难与困厄就好像死寂且粘重的空气,可你必须无时无刻呼吸。抗争的正面是折磨,背面却是灭亡。传奇是对束缚的突破,可传奇从来就不是你我。你觉着胸口有着一口闷气,随即缓缓呼出。
“或许郑先生的晚年其实十分幸福。”你想到。斜阳冲破层云,透过窗子照在了你眼前的画板上。清风徐来,窗外的树木生出了如铅笔勾勒时的沙沙声。你仿佛不觉得心中有着何种的郁结了,在五月温柔且轻盈的空气里,你只是拿起铅笔,笑吟吟的对着画板抬起手去。
只是你自己都没注意到,你半举的右手,微微地有些颤抖。